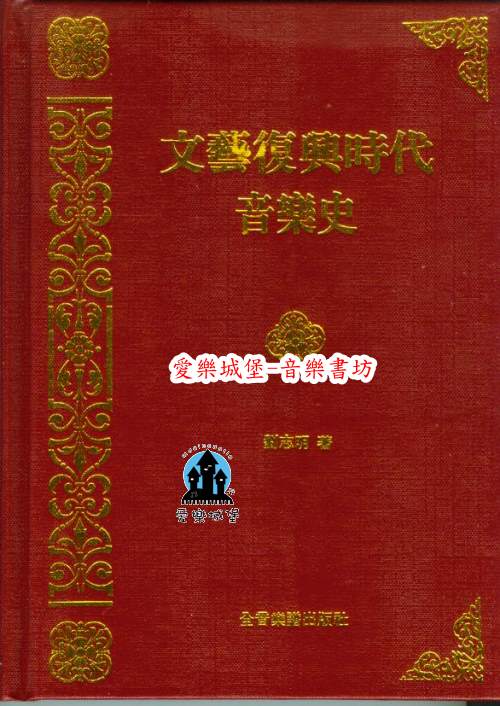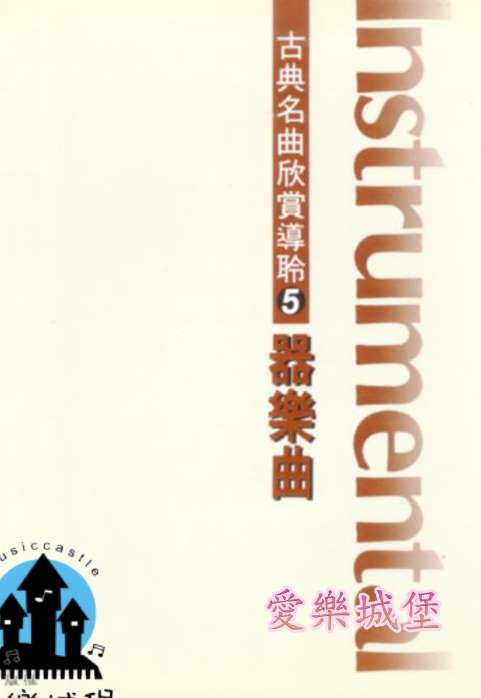|
序 言
這些信札,我相信是從未問世的英文本完整的收集,從幾個觀點看來都是非常有趣的。
這些信札都闡釋了蕭邦的某些創作;他的性格、個性和心理習慣;介紹了他的老師、同事和學生們;註解了塑成他孩童時代生活和作為一個音樂家及男人的整個生命中抑制著他的環境。在這些信札中我們可以看到巴哈與義大利歌劇,波蘭民歌與鋼琴家的技巧所帶給他那衝突性的影響;可以看他對喬治桑的悲劇性的摯愛和他對她的完全不能瞭解;可以看他那清澈明晰的藝術家的天賦,和他在少年時期與法國知識份子生活在一起多年而構成的一種不能更改的狹窄偏見。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家中和家人的愉快相處;他對老朋友熱情的忠誠,以及永不自覺地利用他們;他的激動的脾氣和溫暖的心地;他的諷刺性笑話和他的墨守成規;他對索蘭潔(Solange Clésinger)的親切庇護;他對猶太人和英國人,對出版家們,葡萄牙人和其他同樣低微的人的幼稚卑視;他的動人的謙遜和莊嚴的自尊;以及他對一大群富裕的有閒之士及無頭腦的貴族,憑藉著他們的地位而接納了他們,他的天才使他成為在他們華廈中的一位柔順的非凡之士,也與他們形成了一種「不健全」的關係。
編集這些信札也不是一件易事。對於那些說英語的讀者來說,倘若他們對這些信札中不斷提及的事物和人物並不熟悉的話,無疑會減低了興趣和價值。很多這些事物和人物即使可能加以查證而逐一說明,那將使本書的註解部份超重。因此我在本書中如引用了其他作家的註解,都會以他們名字的簡寫代表,如Op. = Opieński;Karl. = Karlowicz;Hoes. = Hoesick;Leicht. = Leichtentritt。如是沒有簡寫名字的註解,那就是出自本人。
至於提到一些著名的或眾所週知的人名時,如:喬治桑(George Sand),米克里耶維斯(Mickiewicz),洪保德(Humboldt),艾拉果(Arago),林德(Jenny Lind),我認為只要提示他們的生死日期即可,毋需再介紹他們的生平。
有些時候要決定那些資料是有關的和能舉證的,和是多餘的,也不容易。例如說,要分配多少篇幅給那些常常提到的波蘭國事問題呢?那就要看看發生的地點是否與蕭邦的感情有關;或者是發生的地方我根本不知道,甚至懷疑蕭邦是否也知道。他對祖國的熱愛:如對它的言辭,它的諺語,它的幽默,它的歌曲,它的風俗,是毫無疑問的;同時讀者們也不會懷疑到他對久經數世紀被列強侵佔分裂的祖國奮鬥的忠誠同情。然而那份同情卻有著奇異的夥伴。他從未參加過祖國的對抗奮鬥毫不使我們感到詑異;因為風是任意吹的,作為一個創作性的藝術家,不管他對祖國有多強烈的同情,他必須受制於他的藝術而活。但卻使人感到有點驚愕的是這一位波蘭愛國者,不但接受了沙皇送給他的鑽戒,並炫耀於人前,甚至在1831年前更接受了君士坦丁大公爵的恩惠。
更令人撲朔的謎團是在1871年,已故查諾斯基(Stanislaw Tarnowski)伯爵授權一位波蘭大學教授將蕭邦於1831年在斯圖加特所寫的片斷日記(參閱第68封)發表於世,提到了有關得悉俄國軍隊侵佔了並劫掠了華沙的消息。蕭邦當時正承受等待他的親人朋友命運消息的痛苦。我們從他在那一段可怖的時日中所作的樂曲中可以猜想出來;不難相信那時他的靈感會因常常想到他的母親被殺害,年幼的妹妹被酒醉的兵士所蹂躪而受到縈擾分心;但他的日記所記述的,和出自同一隻手,在同一個星期中所作的樂曲卻有著相當的差別。
還有一些關於這個謎團撲朔難明的地方,我曾就教於歐皮恩斯基(Dr. Opieński)有關這些片斷日記的真實性和正確性的意見時,他很快地、謙恭地回覆我說:查諾斯基伯爵擁有得自蕭邦的朋友查托里斯卡(Marcellina Czartoryska)公主這些日記的稿子(是原本呢?或是抄本呢?)。原稿後來卻意外地被銷毀了;但是歐皮恩斯基卻向我保證沒有一位波蘭傳記作家曾質疑過查諾斯基伯爵的稿件;還說他們也從他的音樂中同時引起他們注意到他的心理上的確證,這樣才使我不再對此加以懷疑。
為了使他的信念能使人信服,我把這些日記的片斷列入書內,由於日記本身已不復存在,有關人物亦都死去,所以每位讀者必須自行裁奪是否能將這種事情與他那憤怒激情的d小調前奏曲和c小調練習曲或是極度痛苦的e小調前奏曲來加以協調。人類的心靈是奇怪複雜的,蕭邦可能真真正正地寫下了這些日記。但是要記住,從毫無辦法申辯的死人口中安上那些無聊的話或適當的情感是那麼地容易和清白;甚至蕭邦在生時已有不少有關他的偽造作品在流傳著,就在他死後入土不久,屠格涅夫就發現了他在一處著名的沐浴遊憩地再也見不到任何一位貴族女子,據說「他躺在她的懷抱中喘著最後的一口氣」;因此我只好不全信所有關於他的傳說。
另外一個困難是有關作品的屬性問題。蕭邦似乎實在使用的是一種波蘭民曲的風格,我曾試圖儘可能找出他真正的曲調。盡責的作家似乎都相信一首作品可能受到一首詩詞的啟發,我曾在一些詩詞中找尋參考;但我認為虛妄的或全無根據的把他的作品(特別是馬祖卡和前奏曲)歸附到某些人的名字或某種傳譯,應儘可能加以避免。
蕭邦的四首「敘事曲」就是一個特別的例子。我沒有辦法知道這四首曲子究竟是否有任何確實的證據來證明與詩人米克里耶維斯的名作歌謠有關。但蕭邦與米克里耶維斯是好友;我們知道這位音樂家很受這位詩人的影響,而且很賞識這個歌謠詩詞,因此我有理由相信這首詩在敘事曲內應有一點的地位。
根據柯透(M. Cortot)的說法,g小調敘事曲是根據史詩「Konrad Wallenrod」所寫成;而其他三首則根據米克里耶維斯的歌謠,傳說它們是從立陶宛農人的口中所得資料而寫成;F大調是根據「Świteź」;降A大調是根據「Świtezianka」;而f小調則根據「Trzech Budrysów」。
史詩「Konrad Wallenrod」是一個立陶宛異教徒的故事。立陶宛受到條頓族騎士的侵略,奴役當地土人並強迫他們成為基督教徒。有一位立陶宛人小時候在他雙親被殺害的家中救出,後來受洗為基督教徒並長大後成為德國人,懷著一顆為他族人遭受不公平的復仇的心。他假裝同情德國和信仰基督,在西班牙戰爭中對抗摩爾人而標舉自己,返回立陶宛時裝成一位虔誠及好戰的基督徒,即被選為當地的長官,但至此即故意陷其於毀壞及羞辱之中。這篇詩中唯一以歌謠方式寫出的是那壯麗的「Alpuhara」:一個有關摩爾族酋長的故事,他在被圍困的城市中向西班牙人投降,並宣稱他已轉奉基督教,但堅持要擁抱西班牙軍隊的首領,到這時他才顯露他的真面目並宣稱已帶來西班牙人一次瘟疫的禮物:「看著我,你就會看到你們將如何去死亡。」
另外兩首歌謠則是敘述一個有鬼魂作祟的斯維特茲湖(Świtéź),因為害怕觸怒湖上的荷花神,沒有人膽敢在湖上行舟。這一個湖的名字就述說出諾夫哥羅的俄羅斯人入侵立陶宛一個城堡的故事;城堡的主人因外出就留下女兒負責保衛這個城堡。這位女子無法抵抗來侵的人,只有祈禱神來拯救她和她的侍從免受殺戮之辱。於是湖水吞沒了整個城市,所有的少女都變成了荷花。任何想打破這個湖的孤寂而入侵的人都會發病而死。
「Świtezianka」的意思就是斯維特茲湖的女人,是一個水女神的故事。一名獵人在林中遇到一位少女;她接受了他的愛,但要他發誓忠誠相愛。然後少女離去,他則繞著湖邊走回家中。突然他看見湖的那邊又有另外一位少女,這名愛情不專的獵人竟穿過了沼澤趨前示愛。原來她就是先前那位少女,湖中的水神。她趨前指責他的不忠,很傷心地將他拖到湖裡溺斃。她常被人看到在湖水中舞蹈而那個可憐的男鬼卻在湖邊的落葉松樹下哭號。
「Trzech Budrysów」則是較輕鬆的一首。一位立陶宛異教徒族長布特瑞的三個兒子被他們的父親派遣出外找尋寶藏。他告訴他們三個方向可以找到戰爭及掠奪物:第一個是跟隨著攻打俄國人的酋長,把黑貂皮及銀線衣服帶回來;第二個是加入征討德國的十字軍武士遠征軍,把琥珀及基督教會的祭袍禮服帶回來;第三個是騎馬到波蘭帶回來一名波蘭妻子,因為波蘭的財富中包括了有名的波蘭美女。結果三名兒子都去了,回來時都帶回來一個波蘭新娘。
即使單單是翻譯這些信札也會有困難。因為某些信函是用波蘭文和法文混合寫的,把兩種語文的慣用語法都糾纏在一起;其他有些原來法文的已轉譯為波蘭文,現在又從波蘭文譯為英文;更有一些在早期用法文、德文、拉丁文的學童口語所寫,並有一處是將義大利成語音譯為波蘭文,諸如此類。還有信中用很多諺語及當地引喻,更有幾處含有我在可能範圍內找到的波蘭字典中也查不到的字句。縱然他衷心地輕蔑外國人把波蘭人名拼錯,但蕭邦自己卻是毫不注意對非波蘭名字的正確拼法。他的一貫方法顯然是粗略猜測字的發音,然後就大概地將它音譯成波蘭字。因此,Daily News就變成Deliniuz──但是他也不刻意自己去記住這些,即使是每日在寫的字,他也不去追查曾經是怎樣拼的;所以有時在同一封信中會發現他寫Soliva和Soliwa,Hasslinger和Haslinger,Mendelson,Mendelssohn,Mendelsson等等。
我已盡全力來解開這一團亂麻,試圖保留他拼錯了的字用〔原文如此〕標出,或有時也會把正確的拼法附上加以方括弧說明來幫助讀者瞭解。但如字尾拼錯就不是那麼容易去找出,舉例來說,當一個音譯法文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母是o時,那它原字的結尾就可能是au, aux, ault, aulx, aud, auld, aut等等。
另一個謎團就是波蘭的地名問題。因為這個國家的部份領土曾受到三次外國佔領,歷經數個世代。這些外國統治者都想消滅波蘭的本國語文,一次是想俄羅斯化,另兩次是想德國化,結果是一團混亂,找不出任何滿意的方法。
因此為了要達成這一件賞心但不易達成的工作,稍有一些瑕疵,我在此僅懇求讀者加以原諒。
E.L. Voynich
紐約;1931年6月
|
![西洋音樂簡史 [2024增訂版] 各級音樂班適用~譚琇文 編著 西洋音樂簡史 [2024增訂版] 各級音樂班適用~譚琇文 編著](https://www.musiccastle.tw/public/files/product/S5ff87676149a05c724.jpg)